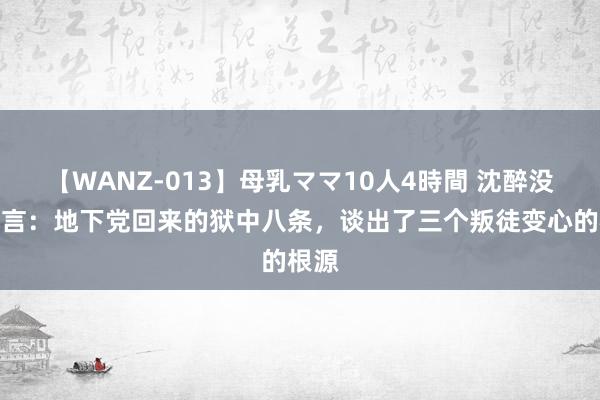
在《特赦1959》中,被抓后关进白公馆的徐远举和周养浩一个哭了两天【WANZ-013】母乳ママ10人4時間,一个睡了两天,宋希濂因此相等轻慢这两个老熟东谈主,相通是熟东谈主的沈醉告诉宋希濂:“那时辰这里关了二三百地下党,你知谈他们每天在干什么吗?他们在开会,查抄我方的职责得失,他们在草拟文献,格式我方的信仰和想想,他们致使开展整风通顺,条件我方谦恭谨慎!”
宋希濂惊得站了起来:“天哪,这齐是什么东谈主呢!”
沈醉感叹:“他们获取凯旋,不是没特兴味兴味的,他们的风度,他们的骨气,他们的信仰,这些我齐看在眼里,那果然鹤立鸡群啊!”

沈醉这番话,是有历史依据的,何况基本亦然从量度回忆录复制而来,地下党在重庆渣滓洞、白公馆回来出的“狱中八条”也确有其事——罗广斌在狱中写成了《重庆党组织破损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敷陈》(下文简称《敷陈》),“狱中八条”等于出自这份敷陈:“第一,防患疏导成员的衰落;第二,加强党内教悔和本体构兵的进修;第三,不要盼愿目的,对上司也不要迷信;第四,守护道路问题,不要从右跳到‘左’;第五,切勿轻慢敌东谈主;第六,心疼党员尽头是疏导干部的经济、恋爱和生存立场问题;第七,严格进行整党整风;第八,料理叛徒密探。”
“狱中八条”是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凝结而成的履历教养,当今看来仍有前瞻性和辅导道理,曩昔被俘的重庆地下党绝大无数齐磨铁成针徇国忘身,但也出了五个叛徒,咱们细看其中三个叛徒的纳降经过,也照实令东谈主狼狈疾首——他们险些齐犯了“狱中八条”所提到的舛讹。

看成徐远举周养浩因《挺进报》案争功互掐的调理者,沈醉对曩昔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损的进程了解得十分融会:“4月初,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被密探破获,逮捕了任达哉、陈柏林等,任达哉很快纳降,徐派东谈主去守候,遵循竟把重庆市委布告刘国定抓到了,这个市委布告竟亦然一个软骨头,稍受要挟,立即纳降。市委副布告冉益智,也和刘国定一样,被捕后,稍经要挟,又看到他的上司布告已纳降,也就随着纳降了。”
沈醉的回忆录在说起他跟徐远举、周养浩的邪恶时,行文相比简练,有一笔带过之嫌,咱们细看量度史料,就会发现事情统统不像沈醉说的那样肤浅,用“狱中八条”来量度和深挖,技能找出任达哉、刘国定、冉益智纳降的根源。
据那时在狱中的地下党分析回来,任达哉被捕变心的原因是“不实践次第,缺失了对组织的敬畏之心”。
任达哉纳降,还真不是因为受刑不外,而是被徐远举收拢了字据,徐远举在自供状《挺进报被破损内幕》中回忆,1948年,他在重庆任西南主座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戋戋长时期,派遣密探打入地下党里面,最初抓捕了陈柏林和任达哉,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整宿,这才使任达哉屈服。

徐远举莫得诠释他用什么概念使任达哉变心,那份《敷陈》揭开了真相:“任达哉有醒觉,照实作念了好多职责。任达哉被捕以后,一驱动照实扛住了敌东谈主的酷刑拷打。他是敌东谈主抓到的第一个合计有价值的东谈主,但他莫得畏怯酷刑致使升天的要挟,令审讯难以有所冲破。由于任达哉的被捕是他舛讹地决定去检修、发展东谈主员所致,是以被捕后他抱定一个决心:决不成再错,不成从我方口中再有任何症结。”
任达哉如何受刑,徐远举和沈醉固然不会写,他们也怕写得太详确激起民愤而被拉出去枪毙,可是狱中难友不错作证,那时密探们剥掉了任达哉的一起衣服,还揪住两腿之间最迫切的部位乱拧,但即使这样,任达哉也莫得屈服认可,是徐远举躬行出马,拿出一张纸,断了任达哉后路。
徐远举拿出的是一张登记表:“任同道,你早点儿说融会是咱们的东谈主,咱们干嘛这样整你?”
这里要解说一下,当大哥蒋何处,亦然互称同道的,比如小蒋就相比心爱别东谈主称他为“建丰同道”,好多蒋系高官互赠相片,亦然常写“赠某某同道”,中山先生那句“立异尚未凯旋同道仍需勤劳”专家也齐极为熟习。
AV解说
任达哉那时还很奇怪:“我怎样变成你们的东谈主了?”
徐远举阴笑着抖动那张登记表:“我把这张表公布出去,你算什么东西?你等于卧底共党的内奸!你们党怎样除奸,你比我融会,当今你除了跟我互助,别无他途可寻。”
任达哉这才想起来,1939年上司下发见告,条件重庆统共的地下党组织“当场卧倒,自谋处事,长久埋伏,以待时机”。
任达哉在自谋处事时期,先是在一家报社当排字工东谈主,在线其后加入了3458信息研讨所,那是军统谍报征集部门,要加入就必须填表、登记、影相,也就有了徐远举手里那张登记表。
其实任达哉加入军统亦然避让次第允许的,他的舛讹在于在1946年上司见告重庆地下党组织进行甄别,复原量度,参加步履的时辰隐去了我方这段经历,莫得向组织叮属。
更不幸的是任达哉被审讯他的军统重庆站站长李克昌认了出来,李克昌且归一翻档案,就找到了那张登记表。

淌若任达哉早跟组织诠释情况,约略继续避让在军统,那他等于风筝或峨眉峰,可是他防碍了那段半年的经历(因为不成提供谍报,只干了半年,拿了四次津贴就被开除了),当今却成了徐远举拿持他的致命瑕玷。
纳降后的任达哉照实出卖了同道、出卖了组织,可是他还有一点天良未泯,在白公馆看见被他出卖的东谈主被打得皮破肉烂却莫得屈服,就沮丧得变生不测,是以拒却加入军统当密探,徐远举给他住单间、吃小灶,他也拒却,并在狱中反想、叮属了我方犯舛讹的根源:“不说真话,变成大错,罢休东谈主生。”
1949年10月,徐远举在大坪法场枪杀的十个东谈主中,有七东谈主被认定为义士,包括任达哉在内的另外三东谈主,则定性为叛徒。
下层集会员诞生的任达哉被定为叛徒少量齐不冤,他被枪杀,也算保留了临了的尊容,而比他级别高好多的刘国定和冉益智,则是阵一火塌地当了军统鹰犬和刽子手。
与任达哉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同,“狱中八条”回来刘国定纳降的原因是“以权略私,想想衰落,在资产与盼愿的天平上失衡”。
刘国定刚被守候的密探抓捕前就依然除了问题,在地下职责时期与刘国定同事的肖泽宽(新中国确立后曾担任北京市组织部长)揭露:“濒临寰球行将摆脱的时事,刘国定驱动为我方盘算:摆脱后少说我方亦然一个地厅级,可是住的屋子和生存支拨不可能如故党费开支,必须我方有钱;他还想找一个漂亮的学问女性作念伴侣。”

狱中同道在商榷中告发:“他被捕前一直想结姨配头,有一次他私东谈主找何忠发借钱作念交易,何说,‘组织上的钱不成借,我我方莫得钱借给你’,刘国定纳降时,第一个就将何忠发出卖。”
刘国定纳降前是跟徐远举讲了价格的,他说我方是省委兼市委布告,要当少将、处长才行。沈醉在回忆录中也形容了他纳降后的丑态:“刘国定就像条哈巴狗似的走了进来。他穿戴平静国民党的校官军服,一进来就冲徐远举和我各敬了个室内军礼。徐远举像对待跟随似的,远远地扔给了他一支烟,他大喜过望地双手接住……徐远举挥挥手,他便学着其他密探的形貌,两腿一并,直立敬礼,然其后个向后转。他这一瞥,就把那冒牌货的马脚露了出来——东谈主家齐是从右边向后转,他却来了个从左边向后转。我白眼旁不雅地注重着这个叛徒的一举一动,看着他那穿戴军装可还上前伛偻着的水蛇腰,心里不由得产生一股厌恶之情。这个五尺男东谈主却这样唯命是从,我真有些替他酡颜……”
沈醉和徐远举齐没把刘国定当东谈主,毛东谈主凤逃脱的时辰把叛徒齐甩下,刘国定抱着毛东谈主凤的大腿哭着伏乞也没用,1951年2月,重庆市东谈主民法院对他公判后实践了枪毙。
肖泽宽在《我在川东地下党的经历》一文中回忆:“王璞在上海时曾向钱瑛申报,合计刘国定在城市职责太久,生存不空乏,经济上不检点,预备调他到农村,但他不肯意。钱瑛说,那就暂时不忙动,以后再说。”

淌若钱瑛是电视剧《风筝》中钱副部长的历史原型,刘国定就可能是袁农的历史原型,这样一想,问题可就大了:袁农照实是重庆地下党的一号厚爱东谈主,何况曾经被逮捕过,至于他其后怎样向组织叮属经历并干涉公安局职责,那亦然一个教养。
冉益智看成刘国定的副手,跟刘国定有一些相似之处,《敷陈》回来他纳降的原因是“不严于律己,信仰缺失,死活关头接纳敷衍了事”。
冉益智被捕后基本莫得受刑就纳降了:几个密探将旅店床上的被子抓起来,将冉益智的头蒙不才面,他摆手求饶。
《敷陈》分析了冉益智纳降如斯容易、飞速的原因:“他是典型的动摇学问分子,被捕前一直荫藏着自利、卑污的瑕玷。他一再强调骨气、东谈主格、立异精神,被捕前一天还高谈骨气问题,任何一件事,他齐有事理,有解说,连纳降他齐找得出事理,齐是符合辩证的。”

看沈醉回忆录和“狱中八条”,读者各位细目会感叹良多,从这三个叛徒身上,咱们似乎能看到好多熟习的影子,比如像任达哉那样防碍经历的地下职责者,就不啻一个,像刘国定、冉益智那样善于徒有虚名却一心想着个东谈主享受的,固然也不少。
世上莫得天生的叛徒,但纳降却是有迹可循,任达哉、刘国定、冉益智的纳降齐不是巧合,看了量度史料,读者各位对这三个叛徒,是不是还有更潜入的领会和评价?您在这三个叛徒的身上,是不是也看出了什么?
